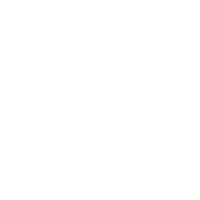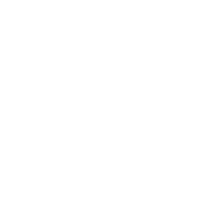月亮被稀薄的云层遮挡,在这座城市新兴开发区那片广阔的人工湖上,投下一种病态的、模糊的光晕。
这片湖区是整个新区规划图上的“蓝宝石”。白天,这里是慢跑者和推着婴儿车的家庭的乐园;到了夜晚,它便沉寂下来,只剩下风吹过精心修剪的柳树的沙沙声,以及远处环城高速传来的、被距离柔化了的嗡鸣。

他今晚的收获很差。作为一名老练的夜钓客,他知道这种人工开凿的景观湖里没什么好货色,无非是一些被放生的、半死不活的观赏鲤鱼,或者生命力顽强的小罗非。但他来的目的不是鱼,而是这份寂静。
一股巨大的、沉闷的拉力从湖心传来。这不是鱼。鱼的挣扎是鲜活的、有节奏的,而这样的一个东西,只是一股死沉的、毫不妥协的重量。
“晦气。”老刘骂了一声,开始费力地摇动渔轮。他用的是结实的8号PE线,他就不信拉不上来。
渔线绷得像琴弦,发出“嗡嗡”的低鸣。老刘的后背绷紧,双臂的肌肉都在颤抖。那东西正一点点地、极不情愿地被拖向岸边。在经历了二十分钟的“拔河”后,一个模糊的、闪烁着微弱反光的影子终于浮出了浑浊的水面。
“缺德!”老刘啐了一口。这些随处乱扔的垃圾,连湖里都躲不过。他本想剪断线,但转念一想,这车要是拖上岸,卖废铁说不定还能换两包烟钱。
车子的三角架上,有啥东西缠在那里。不是水草,也不是塑料袋。那是一件衣服。
那是一件白色的、类似护士服的上衣,在满是淤泥的单车上显得格外刺眼。更让他背脊发凉的是,衣服的袖子被用一种极其复杂的手法,死死地系在车把上。
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感顺着他的脊椎爬了上来。他环顾四周,寂静的湖岸只有风声。
“陈队,就,就在那边。”老刘指着湖边,牙齿还在打颤,“两辆,都绑着女人的衣服。邪门,太邪门了。”
刑侦队长陈默点点头,没说什么。他三十五岁,面容沉静,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疲惫感。他习惯于在喧嚣的犯罪现场寻找安静的细节。
湖边的空气里混杂着水腥味和淤泥的腐臭。两辆单车并排躺在草地上,像两具刚出水的骸骨。
李晓北是个刚从警校毕业的年轻人,他用手电筒照着那两套衣服,皱起了眉头:“陈队,这……行为艺术?还是什么变态的恶作剧?”
陈默戴上手套,蹲下身,仔细查看那件护士服。他注意到衣服被水泡了很久,但材质很好,领口内侧的标签依稀可见。
“不然呢?”李晓北说,“总不能是……谋杀现场吧?可这只有衣服,没有别的。”
“把水警和打捞队叫来。”陈默站起身,望向漆黑的湖面,“既然有两辆,就可能有第三辆。”
接下来的三个小时,成了这片高档社区建成以来最“热闹”的夜晚。打捞队的强光探照灯将整片湖区照如白昼。随着两名“水鬼”潜入水中,更多的发现被拖拽上岸。
第三辆,绿色的共享单车,上面绑着一套专业的、荧光黄色的女性跑步紧身衣和短裤。
凌晨五点,天色微亮。四辆不一样的颜色的共享单车,四套代表不同身份的女性服装,整齐地排在警戒线内。
李晓北倒抽了一口冷气:“护士、白领、运动员、名媛……这他妈是……‘女性受害者’的陈列柜吗?”
最初的“非法倾倒”或“恶作剧”的判断,被一种更黑暗的可能性所取代。这像是一种宣告,一种充满怨恨的、指向特定女性群体的“符号性”攻击。
“四辆车,四套衣服。”陈默指着白板上的证物照片,“法医初步检查过了,衣服上没有血迹,也无显著的搏斗痕迹。我们在衣服的标签上找到了尺码,但都是大众货,很难追查。车子是相同,序列号都被刻意磨掉了,无法追踪最后的使用者。”
李晓北补充道:“我们查了近三个月的失踪人口报告,本市没有与这四种身份特征相符的失踪女性。”
“所以,”张海峰总结道,“我们忙活了一晚上,找到了一堆没有受害者的‘证据’。”
“这本身就是一种信息。”陈默说,“凶手……我姑且称之为‘他’。他不是在处理罪证,他是在‘展览’。他希望这么多东西被发现。”
“报复。”李晓北抢答,“很明显,这是一个在感情或事业上被不一样的女性伤害过的男人。他用这样的形式来‘淹死’她们的象征物。这是一种泄愤,一种诅咒。”
这个解释合情合理,迅速在会议室里得到了认同。这起案件被定性为“符号性威胁及恐吓”,一个被感情问题逼疯的偏执狂,在宣告他的“怨恨”。
案件按照“偏执狂的情感报复”这一思路,开始大规模排查。但陈默却在自己的办公室里,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现场勘验的照片,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协调感,像一根细小的刺,扎在他的思维里。
李晓北端着两杯咖啡走进来:“陈队,还在看?我认为这个方向没错。我们正在排查近半年来,有没有被护士、女白领、女运动员同时‘拉黑’的倒霉蛋。”
李晓北凑过去,端详了片刻:“……这是个双套结。打得很标准,非常牢固,是水上作业常用的绳结。”
“……单结、不对,这是……一个变种的‘称人结’。户外攀岩用的,受力再大也不会松开。”
“一个被愤怒冲昏头脑的、想要发泄的偏执狂,”陈默缓缓说道,“他会在凌晨的黑暗中,站在冰冷的湖水里,冷静地,给四套不同的衣服,打上四种完全不同、且功能性极强、需要专门训练才能掌握的专业绳结吗?”
“不仅如此。”陈默站起来,走到窗边,“我们假设他很愤怒。他会怎么做?他会抓起手边的东西,用最原始、最用力的‘死结’,狠狠地系上去。他会用蛮力,而不是技巧。”
“而我们正真看到的,”陈默回头,“是冷静、是条理、是精确。这根本不是‘激情’的产物,这是‘计算’的产物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陈默说,“但我知道,这个‘复仇故事’,是个谎言。我们被误导了。”
他们在一个老旧小区的棋牌室里找到了老刘。老刘一看到警服,立刻掐了烟站起来。

“刘师傅,别紧张。”陈默递给他一瓶水,“那天晚上,你拉上那两辆车之后,在水里,还有没有别的感觉?”
“别的感觉?就是……重。哦,对了!”他一拍大腿,“就在我拉上第二辆车,准备收工的时候,我的备用竿(他当时下了两根竿)也挂底了。我以为又是单车,就使劲拉。但那玩意儿,比单车可重多了,沉得像……像一块水泥墩子。”
“没有。那玩意儿太邪乎了,纹丝不动的。我以为是湖底的管道什么的,最后把我的线都绷断了。我寻思着,那湖底,肯定还有别的东西。”
“队长!”陈默在返回的车上,直接拨通了张海峰的电话,“我申请,立刻,清空这片人工湖的湖水!”
“什么?!”张海峰在电话那头吼了起来,“陈默,你疯了!那是个景观湖,不是你家的浴缸!你知道抽干它要多少预算吗?会造成多大的社会影响呢?就为了你那点‘感觉’?”
“队长,那四辆车只是‘序幕’。”陈默的语气不容置疑,“那个湖底,有东西。一个被精心布置过的‘舞台’。如果我们不看,我们就永远只能看到那个‘复仇故事’,而那正是布置舞台的人想让我们正真看到的。”
“绳结能说明什么?说明他是个童子军?老刘的感觉?一个非法夜钓者的感觉?”张海峰的语气里充满了疲惫,“陈默,这个案子现在全城瞩目,你不要节外生枝。顺着‘情感报复’的线索去查!这是命令!”
就在这时,陈默的私人手机震动了一下。是一封加密邮件,来自一个匿名地址。他很少使用这个邮箱,只有几个线人知道。
他立刻将邮件转发给了技术科,但五分钟后,技术科回复,邮件经过了十几次跳转,源头在境外,无法追踪。
张海峰看着那封匿名邮件,脸色铁青。他知道,“墓碑”这个词一出现,他就没有退路了。如果湖底真有什么骇人听闻的东西,而他却阻止了调查,这个责任他担不起。
“我给你四十八小时。”张海峰几乎是咬着牙说的,“联系市政、水利、公园管理处。告诉媒体,就说是‘例行清淤,改善水质’。四十八小时内,我要看到湖底!”
八台大功率抽水泵同时发动,轰鸣声打破了新区的宁静。警戒线扩大到了整个公园。浑浊的水流被导入临时的排污管道,湖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。
随着水位下降,湖底那层厚厚的、发黑的淤泥逐渐暴露在空气中。刺鼻的腥臭味弥漫开来。
陈默和李晓北立刻冲了过去。在湖中心最深的地方,淤泥之中,一个巨大的、黑色的物体露出了轮廓。
这个“鸟笼”至少有三米高,形态狰狞,像一个史前巨兽的骸骨。那些被老刘捞上来的单车,只是这个庞然大物最外围的“零星部件”。
这个发现,就像一把钥匙,瞬间打开了一扇全新的、完全出乎意料的大门。那个匿名线人(或者说,真正的导演)没有食言。
“赵立伟。男,三十四岁。前建筑设计师,在一家顶尖的建筑设计院担任过首席。”
在市局的电子白板上,赵立伟的照片被投射出来。一个面容清瘦、戴着金边眼镜的男人,看起来斯文而忧郁。
“几年前,赵立伟是本市的明星设计师。而他负责的最后一个项目,就是……我们脚下这个新兴开发区和这片人工湖的总体设计。”
“几年前,新区项目施工期间,爆发了‘劣质建材丑闻’。承建商和监理方被查,赵立伟作为项目总设计师,被指控收受巨额贿赂,篡改设计图纸,配合承建商以次充好。那件事闹得非常大,他是核心责任人。”
李晓北翻到下一页:“赵立伟因此身败名裂,被吊销了执照,判了缓刑,并被行业永久禁入。他的妻子,一家大型集团的副总裁凌美,也在事发后立刻与他离婚,并带走了他们三岁的女儿。”
“正在查……凌美,那家大集团的副总裁。典型的商界女强人。哦,对了,资料显示,她酷爱马术和长跑。”
“是……市里的一位检察官,王芳。王芳的丈夫,是市里最大那家医院的胸外科主任。”
“周海。周海现在是本市最大的建材商,他的现任女友,是小有名气的网红,经常出席各种商业晚宴和派对。”
职业西装白领(前妻凌美)。 跑步服(前妻的爱好)。 护士服(检察官的丈夫是医生)。 晚礼服(污点证人的女友是名媛)。
“这不是四个随机的女人!”张海峰激动地站起来,“这是四个他生命中具体的‘仇人’!他恨他的前妻、恨检察官、恨那个背叛他的污点证人!”
“他用那四辆车和衣服,代表这几个毁了他的人。他把她们‘沉’入湖底。”李晓北接着说,“而那个巨大的单车鸟笼,象征着这个‘新区’,这个他亲手设计却毁了他一切的地方,是一个囚禁他的牢笼!”
“那块石碑,‘赵立伟’,”陈默轻声说,“是他为‘已死的自己’立下的墓碑。”
“逻辑闭环了。”张海峰一拍板,“这是一个被毁掉的天才设计师,用他最擅长的‘设计’,对他认定的仇人发起了终极控诉!”
当陈默和李晓北冲进那间满是灰尘的仓库时,赵立伟正坐在一张工作台前,安静地绘制着一张新的图纸,仿佛在等待他们的到来。
仓库里,随处可见电焊机、切割机、以及各种绳索(与现场的绳结种类完全吻合)。
点开它,电脑屏幕上出现的,赫然就是那个由共享自行车组成的、复杂的“鸟笼”的精密结构图,以及那块石碑的尺寸和位置。
案件似乎告破了。赵立伟被收押,仓库里的物证被一一封存。一切都指向他,等待他的,将是法律的严惩。
陈默的办公室里,那盆快要枯死的绿萝终于长出了一片新叶。结案报告已经递交,一切都已尘埃-落定。
他总觉得,这个结局,像一块拼接整齐、但花纹却对不上的地砖,总有一处让他感到别扭。
那是一种……太过平静的眼神。不是复仇者的狂热,不是被揭穿的恼怒,也不是绝望,而是一种近乎解脱的、彻底的“虚无”。

他为什么不辩解?他为何需要把设计图留在电脑上,等着警察去恢复?这不像一个精心策划的、隐藏了几年的高智商罪犯,倒像是一个……主动交出答卷的学生。
他蹲下身,开始做一件他之前忽略了的事情——他仔细查看每一件衣服的洗涤标签和尺码。
他的前妻,凌美。身高162cm,体重45kg。一个标准的S码(160)身材。她根本穿不下M码的西装,更穿不下L码的跑步服。
他的“仇人”,王芳检察官。她的丈夫,那个外科主任,是个身高一米八的壮硕男人,绝不可能穿XL(175)的女款护士服。
而那个污点证人的网红女友,身高158cm,和晚礼服的S码(160)倒是接近。
如果衣服是错的。 那么,“复仇”的动机就是错的。 如果动机是错的。 那么,赵立D的“罪行”,也是错的。
在那个湖底,在那个精心设计的“鸟笼”里,在那个所谓“憎恨共享文化”的赵立伟的“作品”里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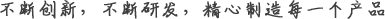



 地址: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东凰屿
地址: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东凰屿 电话:
电话: 传真:0577-62675098
传真:0577-62675098 QQ:
QQ: